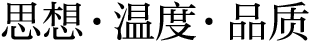编者按:4月18日,长影乐团作曲家、电影音乐家吴大明在长春病逝,终年89岁。从事电影音乐创作的四十年中,吴大明先后为电影《苦难的心》《残雪》《绿色钱包》《人到中年》《勿忘我》《16号病房》《今夜有暴风雪》《黄山来的姑娘》《蒋筑英》《留村察看》《喜莲》等四十多部影视作品配乐。作为吴大明的学生,中央音乐学院教师、盲人作曲家代博特别撰文,悼念恩师。
从今年起,每年的4月18日,之于我又多了一层特殊的意义,多了一条唤起回忆的纽带。2001年的4月18日,我踏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招生考试的考场。用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来说,我自此开始了我的音乐生涯。今年的4月18日,我的恩师、作曲家吴大明先生溘然长逝。有关他的讣告上,大多会提及《人到中年》《残雪》等由他配乐的电影。这当然是因为这些影片,尤其是其中的电影插曲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但对于熟识他的人来说,他个人承载的绝非“一位电影音乐作曲家”所能概括,而他在我身上刻下的烙印更非寥寥数言所能企至。
“时隔许久,我才慢慢意识到,那时的我何其幸运”
我随吴老师上课的时日,只是1997年9月到1998年11月的短短一年多。看似不甚长久,且远在我进入音乐学院附中以前,但又有谁能用这些标度时间来臆断一个孩子可能从中受到的深远影响呢?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第一次来到吴老师家中。尽管彼时的我只有9岁出头,但在音乐方面却不乏自信。我在钢琴上已经即兴写出了几首“变奏曲”,且平日里听到的都是来自各方的夸赞,说我才华出众云云,但吴老师对我想学作曲的热情似乎不以为然。一见面就和我说,“作曲很累的,你可能付出了非常多,但得到的东西完全不能与之相匹配。”“作曲也不是你有兴趣就坚持得了的,况且坚持下来也很可能没有你想象的美好结果。”我对这种说教同样不以为然,表示我无所畏惧。随后发生的事我终生难忘,吴老师在他庞大的书架上拿出几张唱片,并依次播给我听。它们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勋伯格的《一个华沙的幸存者》、潘德列茨基的《广岛死难者的挽歌》和古莱茨基的《第三交响曲》。然后他说道:“这是二十世纪的音乐,你还想作曲吗?”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受到的刺激不小,但不知一股什么力量促使我语气更加坚定,答道:“我还是要学。”他见此轮劝退未遂,便约次日与我父母单独详谈。整个过程反倒使我原本懵懂的意识变成了某种坚定的信念,最终,吴老师答应先给我上五节和声课再说。换句话讲,成为他的学生还得有试读期。后来我才明白,他根本不收学生。这对他而言已经是破例了。时隔许久,我才慢慢意识到,那时的我何其幸运。
吴老师的和声课虽然在进度上大体遵循斯波索宾的架构,但所举范例却来源丰富。他参考辟斯顿、盖丘斯、凯思特莱尔、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等人的和声书,还不断找出一些原文的和声学专著。每次课他都为我一个人编写专门的教案,对于书上给的例子他常会发表集聚批判性的观点,并指出哪些和弦还可能有更好的选择。更加令我没想到的是,每次上课,他在评述过我的作业后会拿出他自己的版本与我对比。且大多数时候,他都写出了多个版本。这使我不知不觉地也开始思考多种方案。渐渐地,为同一条旋律做不同的和声诠释成了我的习惯。在初识和弦外音时,我显然遇到了一些瓶颈,总是会对和声的方向做出错误的判断,吴老师对此是一丝不苟的。一次,我做了一个“漂亮”的平五加隐伏五度进行,吴老师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该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最后的“处理方案”是,我把和弦外音那十章的题有选择地又做了一遍。
在教我和声的同时,吴老师还坚持每次课给我讲一些音乐史方面的内容。当时我家里只有录音机可以听,他就每周给我转录磁带听。这数十盒磁带涵盖了从维瓦尔第直至里姆的大量不同风格作品,不仅让我对西方音乐史有了全景式的“鸟瞰”,更重要的是,让我对不同的风格怀有包容的心态。这其中有两盒“二战”后的先锋音乐,包括从一开始就令我着迷的武满彻和鲁托斯瓦夫斯基,和我至今也喜欢不起来的凯奇。但无论如何,我能用一种平和的心态面对他们,既不拒斥,也不猎奇。

“他培养了我观察不同演奏诠释的思维和角度”
在他给我讲音乐史的过程中,有一个场景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一次下课后,我表示想多听点穆索尔斯基的作品,他便拿出了《鲍里斯·戈杜诺夫》给我听,我顺嘴问了一句:“这作品哪年写的啊?”他看了一下CD的唱片内页说:“1874年。”然后,略略迟疑了一下,他放下唱片,缓缓走到了书架前,拿出了格罗夫音乐辞典,并仔细翻阅起来。过了半晌,他慢慢说道:“1874年是这部歌剧首演的年份,但关于他开始创作的时间,不同资料有不同说法。”然后详述了有关种种。我第一次知道,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还可能有不止一种答案,这么小的事儿也要去看这么厚的辞典。而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随意提出的问题抱有如此的耐心,我至今难以企及。
在给我翻录磁带的年月里,吴老师也把每首曲目的独奏家、乐团和指挥写成磁带内页发给我,并且会告诉我为什么选择这个版本而非那个。有时他甚至会就内田光子与吉塞金对德彪西钢琴练习曲的不同处理发表长篇大论,由此培养了我观察不同演奏诠释的思维和角度。
相对于吴老师对和声写作的一丝不苟,他教授作曲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只经历了两次模仿写作的训练,他就开始鼓励我跳脱出那些我学过的思维定式,把和声课讲的条条框框放在一边,尽一切可能,打开自己的思路,努力找寻自己的“声音”。这令我很是挠头,刚刚在和声训练中建立起的信心又得重新经历考验。
在完成了调性和声的学习后,吴老师还给我上了一系列乐器法的课程,其中运用了大量的谱例和音响,他还对每种乐器发表了他写作时的经验之谈。平心而论,吴老师讲的乐器法实用、有效,但多少有些过度谨慎,恐怕这与他长期生活在长春这个音乐上的三线城市不无关系。
“他是我作曲学习的一面镜子”
至1998年底,我与吴老师每周上课的时光告一段落。每次上课都有上满一整个下午的趋势,加之为我备课付出的精力,一方面,他的身体开始愈发吃不消;另一方面,他也催促我寻求更好的学习平台。我却又等了近两年才做出离开家乡、赴京求学的决定。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会定期向他汇报我的学习进展,但得到的回应大多是:“这说明不了什么。”钢琴考级得了优秀说明不了什么,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也不能代表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要做到怎样才能让他觉得的确发生了什么。相比于此,他对我的作曲学习却总是一面镜子。当我迷恋于晚期浪漫主义的半音化和声时,他提醒我要跳出传统的藩篱。当我沉浸于模仿那些特殊演奏法不能自拔时,他告诉我调式和声还有许多层面可以开发。当我整天浸泡在西方音乐的海洋中,他提醒我多听听中国的地方戏曲。当我为了比赛能够获奖强行在内省性的作品中插入炫技段落,他又提醒我多考虑考虑“你的音乐需要什么”。
无论如何,在我上大学之后,我从他那里听到的正面评价开始愈来愈多了,但我已不像年少时那样通过他人的肯定获取自我认同了。相反,我更愿意简单地成为一个倾听者,而吴老师也开始成为我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他教我的和声确保我免修了附中和大学前两学期的和声课,对音乐史的细致多角度思考也成了我的学术习惯,至于多听音乐这件事儿最终把我变成了和他一样的唱片控。我时常和他通话聊唱片,聊音乐史研究,甚至足球,他对一些事物的认真和敏锐度似乎是永不改变的。2011年,我正在写有关席曼诺夫斯基的研究论文。一次与他聊起席曼诺夫斯基交响曲的不同录音版本,他提到了企鹅唱片指南上的一些评价。我就顺便问了一句,企鹅唱片对这些录音的评价在这几年里有什么变化趋势吗?结果,他貌似把这当成了一个学术课题,过了一段时间,给我总结了大量的资料并配以对比分析,令我感到不知所措。而在2019年,我最后一次拜访他,当我聊起雅纳切克《狡猾的小狐狸》组曲与歌剧原作的配器差异时,我误把组曲的配器者说成了安淇尔,他在一旁轻声提醒我:“是塔利赫。”
“吴老师的淡泊名利近乎到了偏执的程度”
除了这些常备的话题,我听到最多的,是他对往昔的回忆。他讲他与沈湘先生一起在图书馆整理唱片的年月,讲当年江文也先生的配器课,讲他如何翘了苏联专家的课去听姚锦新先生讲作品分析,讲他刚被错划成右派时萧淑娴先生对他投来的橄榄枝,尤其是他跟随蓝玉菘先生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故事,他甚至在晚年投入数年时间整理了蓝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以纪念蓝先生的学术贡献。现在想来,这其中的每个故事都含着太多寥寥数语背后的难言之隐。每个人和事都背负着历史的沧桑,而他作为一位历史的参与者注定见证了一些个人不愿记起而后人又无法共情的过往。有时,他也讲些令人感到轻松的经历,如随剧组采风、随研究团队去敦煌考察,甚至偶尔说说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小学音乐生活,但就是从来不聊他那些一度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
在一个传播手段飞速便捷化的时代,就连“淡泊名利”这样的表述都有成为外交辞令的趋势,而吴老师的淡泊名利近乎到了偏执的程度。他拒绝一切形式的个人宣传,推掉了一切的媒体采访。对于要把他写入中国当代音乐史的学者,他也敬而远之。他对大师们的作品如数家珍,但诸如雅纳切克是如何一边鼓吹捷克民族独立,一边绞尽脑汁促成《耶努法》于1918年2月2日在维也纳的演出并不是他研习的榜样。因此吴老师早早地被公众遗忘了。准确地说,除了他配乐的那些影片,他从未进入过公众视野。他对音乐的热爱是纯粹的,纯粹到不用它换取任何物质财富。尼采那句“音乐不是实现任何目的的手段,音乐自身就是目的”,在他这里得以完美的体现。
如今,吴老师已经带着他的才学、他的纯粹、他的那些故事去了另一个世界。每当我回忆起当年和他上课的时光都恍如隔世。我记起的不只是他的严谨、认真与敏锐,而是每当我看着他打开那些写着英文、法文、俄文、匈牙利文的书籍和唱片时都能感受到一个时间与空间无限广阔的世界,一个我需要努力才能触及但却包含着人类伟大智慧与灵感的世界,一个我能在其中找到“爱”的世界。这个世界超越任何人的生命一直延续着,一直闪烁着光芒。如今,他离开了我们,却把这个“无比美好的世界”留给了我。吴老师,一路走好!
代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