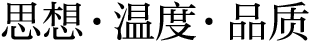2003年,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萧梅带着青年学者杨晓在贵州侗寨田野调查,为侗族大歌申报联合国非遗名录做前期准备。坐在火塘边,萧梅回想起音乐界前辈几十年前肩负少数民族调查、音乐集成等任务一再探访侗寨,对杨晓说,“如今的非遗行动是再一次‘摸家底’或又一次整理国故。”
21世纪初,我国在认同联合国《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的基础上,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中国国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为背景,自上而下贯穿覆盖全国各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
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传统音乐项目,在某种程度上结束了“民间”身份,成为国家文化工作的重要关注对象。而非遗之后,它们的命运如何?
2014年,萧梅、杨晓组建“非遗之后”课题组,由曾河、刘盼盼、杨晓、李亚、钟隽迪、李伟、卢婷、秦思、魏有鲲、吴双、凌嘉穗、尹翔等青年学者和学生,分别对11种非遗项目的生存现状进行深度观察,完成每个单项项目调查报告。其成果《非遗之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类)考察研究》于近日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传统音乐的第三次“摸家底”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中国非遗工作的十六字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要求各地区要进一步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认定和登记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及时向社会公布普查结果。
“在‘非遗’这个概念下大规模体系化的整理行为,应该算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第三次面向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国家行为。”萧梅介绍,1950年以来,我国对传统音乐进行过三次大规模整理,除编修国故外,还具有建设中国音乐现代知识体系的明确目标。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省区市就成立“音乐工作组”和“戏曲工作组”,对各地传统音乐进行“摸家底”式的系统搜集,为中国各民族音乐现代知识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第二次大规模整理,是1979年开始,历时三十年完成的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共4.5亿字450册。其中,民歌集成、戏曲集成、器乐集成、曲艺集成、舞蹈集成等八部直接关系到各种类型的传统音乐。
21世纪初兴起的“非遗行动”,以前两次整理为基础,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非遗的生存环境、运用的文化空间和传承状态等方面。“我们看到非遗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国策,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再认识再表达的过程。”萧梅说,二十多年来,在政府、民间、学校、学界、文艺界、商界的多重合力之中,传统音乐以非遗之名再度历经洗礼。
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我国基本完成了针对中国非遗项目的一系列政策性方案的基础建设,并以此为依据在全国铺开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为主要线索的非遗行动。
2014年,萧梅、杨晓组建“非遗之后”课题组,“我们想看音乐文化在成为非遗之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长期田野调查中,课题组成员不断变化着观察者、评价者、参与者这三种身份。

曾河与李伟的田野历程是特别典型的民族音乐学的“跳出”与“融入”。曾河作为一个具有家传背景的古琴演奏家,通过理论学习并以重建数据的方式跳出局内人的纯感性认知,以观察者、评价者的身份审视古琴。作为一个音乐学理论专业学生,李伟则通过长时期深度田野调查,从局外融入到局内,成为项目参与者。
如果不是“非遗之后”课题,李伟也许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四川扬琴。他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走进四川扬琴茶馆时的惊讶,“观众年纪大得超乎想象。”看到年轻人进来,大家都很兴奋。一位老观众对他说,“小伙子,你来听嘛,听了要上瘾哦。”李伟不以为然,心想,“我是来拿资料写论文,写完要走人的。”他每周预习唱本后来茶馆听,听天书一般坚持了近两个月,竟然慢慢进入状态,最后真的“上瘾”,连身份也从理论研究者变成演唱演奏者。

为了全面了解四川扬琴,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李伟拜师刘时燕,跟随刘时燕学习女腔演唱和鼓板演奏,跟随李卷怡学习了四川扬琴中三弦基本演奏技巧,跟随林同清学习四川扬琴伴奏手法和男腔……2015年开始登台,其后参加比赛并屡次获奖。身边的同事、朋友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四川扬琴的传承。2019年,四川省艺术研究院策划的四川扬琴传承人收徒传艺传承保护工作中,李伟、刘婷婷、彭勇、杨夏、胡郦珈、张盈等青年演员在一年时间内完整掌握了两个以上四川扬琴传统曲目。“四川扬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小众的艺术,是一个需要充足的时间来消磨的艺术,是一个需要较深的文化沉淀且能让人上瘾的艺术,而不仅仅是专属于老年受众的艺术。”李伟完成了“非遗之后”报告《四川扬琴非遗保护调查》。

四川扬琴之外,“非遗之后”还收录侗族大歌、上海港码头工人号子、彝族海菜腔、嘉禾伴嫁歌、拉姆户歌谣、粤东碣石竹马戏、古琴、江南丝竹、觉囊梵音、滇剧等共11个不同层级的非遗项目,涉及分布在中国西南部、长江中下游与中国台湾地区的五个族群——汉族、侗族、藏族、彝族、台湾泰雅族。其中,侗族大歌、码头工人号子、海菜腔、伴嫁歌、拉姆户歌谣、竹马戏,是伴有重要民俗仪式的歌唱活动;古琴、江南丝竹,是活跃在近现代城乡生活中的典型器乐乐种;觉囊梵音是藏传佛教仪式音声;四川扬琴、滇剧,是传承了二百余年的民间说唱艺术和戏曲艺术。


课题组遵循四个原则:多维度数据采集、定量定性兼容、一手二手对话、共时历时交织。其中,多维度数据采集是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的基本工作方式,指对田野对象的全面体验、认知与数据整理,也强调资料形式的多样性,即图、文、音、像、物的全面性。“我们想用数据说话、在现场讲话、请主体对话,通过跟踪典型的非遗名录项目在非遗之后的命运,更深、更广地理解这个众口一词又争议不断的非遗化过程,深度观察‘非遗之后’传统音乐项目的当代生命样态。”经历了“非遗之后”,杨晓更真实地体会到非遗在中国的复杂性,对中国非遗这个命题有了深刻理解。
谁是传承人

保护代表性传承人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为保证传承人更好地开展传承工作,提高传承人积极性,政府每年发放相应补助。但是这个善意的制度在行使过程中遇到了重重挑战,尤其在表演类非遗项目中可谓倍受争议。
二十年来,“谁是传承人”一直是传承人制度的核心问题。“非遗之后”课题中,“谁是传承人”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开始认定前,杨晓接到一通电话。一位侗族大歌歌手非常焦急地向她咨询,申报传承人究竟需要什么条件,“我们地方上原来把那些特别会编歌而且肚子里记歌记得多的人喊‘歌师’,但实际上,现在真正使侗歌在外面有影响力的人是我们这些唱歌唱得好听又能教歌的人,我觉得我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传承人。”
侗歌传统的核心能力是歌师对歌词的记忆与创编能力,而非歌手个人的歌唱能力。因为侗族人多声部歌唱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长时间丰富的歌唱仪式强化传统社会结构。认定具有哪种能力的人才是传承人,决定着该项目之后的传承内容与传承路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发展走向。
这位歌手的焦虑是传承人认定中的普遍焦虑。在绝大多数传统表演艺术中,表演者本身就是不同程度的创编者,展演过程本身就是创编过程。这种在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复合创演能力,在当代社会急速脱落,对传承人的认定提出了新的挑战。“传承人究竟应该是非遗的创编者、表演者、组织者抑或是其他角色,体现在不同的个案项目中,答案不应该是统一的。”萧梅说。
非遗传承人制度还存在“个体传承人制度与群体性非遗项目之间的矛盾”。“非遗之后”11个项目里除了古琴之外,其他10个群体参与方式的项目都明显体现出二者的冲突。在同一个表演群体中,那些没有传承人称号的乐社歌班成员常因没有获得同等对待而十分沮丧。
李亚表示,江南丝竹表演机制以“合乐”为核心,丝竹乐的习得通常以“社”为载体进行,作为一个器乐合奏乐种,目前以个体为主的传承人制度难以实现乐种的有效传承。李伟调研四川扬琴时,将采访的传承人分为两类,“有传承人身份传承人”与“无传承人身份传承人”。他强调后者虽没有非遗传承人的身份,但仍然是传承人,采访他们时感受到更多的是怨气与无奈。“怨的不仅仅是一年几千元的传承经费,而是政府并没有给他们一个相同的身份认同。”李伟说。
与此同时,具有传承人称号的人心里似乎也不轻松,需要面对这一头衔带来的诸多挑战。海菜腔传承人后宝云从前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吃火草烟的玩场上习得的歌舞技艺居然可以在大城市表演。登上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舞台后,他的心里发生了微妙变化,产生了要当“艺术家”的想法。“即使没有成为艺术家的愿望,传承人也会在自我定位和生活方式上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杨晓采访过一位烟盒舞传承人,他常外出参加活动,现在心里总想着如何有更多机会展示技艺,如何把技艺练好,时间久了觉得种田真的辛苦,一下地就头疼。
“接受这种半官方化身份的同时,意味着传承人要承担传承、展演、传播等多种责任与义务,并挤压其他日常生活与日常劳作的空间。传承人制度的初衷究竟是培养职业的传承者,还是在传承者不脱离原本生活方式的前提下提供一定的传承保障呢?”萧梅就此提出了一系列疑问。
如何保护,怎样传承

“如何保护”“怎样传承”是课题组面临的又一道基础题,在理论与实践中都有着超乎想象的复杂性。
2015年9月,在“第三届海内外江南丝竹邀请赛”现场,李亚连续两天听了二十多支江南丝竹乐团的演奏,每个团队都尽可能表现音乐艺术的完美,音准精确、音质纯净、速度平稳、声部有序,听起来整齐划一、千篇一律。但是一家民间乐社的演奏引起她的注意。
这家乐社演奏的《行街》是其平日聚会时反复演奏的传统曲目,但这次舞台呈现与平日不同。李亚颇感意外,在笔记本上记下自己的感受:“《行街》的速度忽快忽慢,尤其在快板部分,琵琶的音总是提前冒出来……”原来,该社的琵琶玩家由于个人原因未能参赛,替补选手属于“江南丝竹”里的浦东派,平时较少与他们合作,因此有了这次不尽人意的表演。
“相比其他团队的表演‘正确’,看似‘失败’的《行街》恰恰是民间乐社的真实状态。”李亚介绍,江南丝竹的每一次“合乐”都是在“搿”(合)的过程中建构、调节彼此间的关系,90%的演奏都是不甚满意的,完美默契的演奏需要通过很长时间的磨合才会得以实现。
“江南丝竹”民间乐社的即兴演奏,与学院建制下的专业体系、职业表演的“程式性”“规范化”演奏手法有着根本差异。目前,“江南丝竹”的非遗保护重要举措之一是创作新作品。在新作品推广活动中,李亚看到的是在“江南丝竹”这一名称下的各类形式的民族器乐舞台表演,民乐二重奏、二胡、竹笛独奏、民族大乐队合奏等皆被视为“江南丝竹”。
而民间玩家几乎不会演奏这些新作品。一位丝竹玩家认为,新作品就是“民乐小合奏”:“演奏这些作品,实际上是简单的,因为它是不能变化的,不能改动的,要按照作曲家的意思来,我只要把谱子上的音符演奏出来就行了。但是江南丝竹不一样,它时时在变,要求你表达你自己脑袋里的东西,表达你自己的个性。”
在对“江南丝竹”进行深入调查后,李亚不禁思考:谁是江南丝竹的文化主体,政府、音乐精英还是民间玩家?江南丝竹需要保护与传承的是什么,曲目、音乐风格、乐社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调研湖南嘉禾伴嫁歌的吴双。成为非遗项目前,伴嫁歌主要流行于民间伴嫁仪式中,是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的艺术形式。申遗之后,嘉禾县开展大规模民歌征集活动,收集新创民歌,举办文艺汇演和民歌比赛等活动。舞台化的伴嫁歌与民间伴嫁仪式中的伴嫁歌存在诸多区别。比如,舞台上伴嫁歌是经过排练的固定化演出,而仪式中的伴嫁歌有一定即兴成分。非遗保护对嘉禾伴嫁歌产生积极影响,也限制了它的发展方向。“非遗到底是谁的非遗?谁是非遗保护的主体?非遗保护的执行者是谁?”吴双认为,伴嫁歌知名度不断提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越来越多。
为了探究“如何保护”“怎样传承”,课题组梳理出六种非遗传承传播空间。每种空间中,非遗项目由不同的传承传播者面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传承传播。其一,原生语境中的原生态传承传播,如村落中的传统民俗;其二,修复原生语境中的传播,如在地化的非遗基地乡村旅游;其三,新民俗中的舞台化传播,如乡镇以上级别的非遗节会与传统节会;其四,文艺团体中的舞台化传承传播,如各级各类歌舞团、文工团;其五,学校中的舞台化传承传播,如高职高校的非遗专业、非遗进中小学课堂;其六,再造语境中的舞台化传播,如风景区与博览园中的非遗展演。
通过深入传统音乐生命的现场,学者们与传统音乐命运共情,并由此理解传统在当代复杂的生命状态与生存空间。“如何从研究中跳出来,以相对客观的立场分析现象”也在调研过程中不断被反思。课题启动之初,萧梅便强调应尽可能采撷数据而不是发表个人学术观点。课题组成员以考察中观察到的具体保护措施与获取的数据呈现非遗保护中的问题,用丰富的资料说明非遗对于音乐文化发展与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者能否成为文化当事人与政府之间的黏合剂?如何在学理上作出贡献,而不是在意识形态中讨论问题,这是围绕‘非遗之后’值得思考的问题。”萧梅说。
卢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