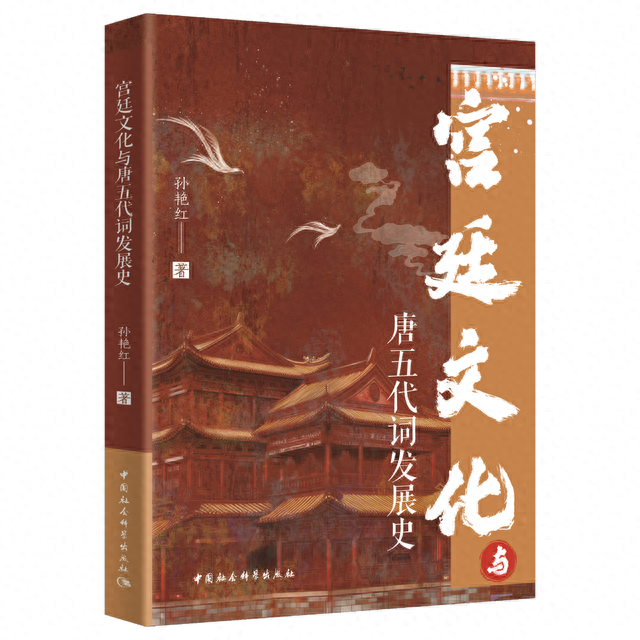2023-09-21 20:36
来源: 北京号
文体学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而深厚的文体学思想,而且成熟相当早,《文心雕龙》的文体学已经相当精深而有体系,此后一直到清代,文体学久盛不衰。”其实中国文体学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就已经提出“四科八体”之说,晋陆机《文赋》列叙了十种文体,分别指出它们的不同风格特点。而刘勰《文心雕龙》则对文体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论述。郭英德先生曾经强调 : “中国古人对文体进行自觉的、系统的分类,并且形成特定的文体分类观,大致始于魏晋时期。但是,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人就对文体的分类进行了许多实践的操作和理论的思考,从而逐渐形成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的雏形。”正是因为我国古代有这些文体学方面的论述,我们在研究学习过程中才更为关注各种文体的源流与发展。但“目前关于诗词曲起源问题的探讨,不少是基于一种预设立场,即文体是独立孕育、发展的,且从开始就具有一个确定不移的本质性特征,这种特征具有唯一性与排他性。事实上,无论诗词曲还是其他文体,从来都没有这样一个确定不变的本质特征,只有相对的时代标准或文类划分”基于此,我们在讨论词的起源问题时才出现了多种说法,甚至至今仍是千古谜案。
黑龙江大学的陶尔夫先生在《论宗教与词体的兴起》一文中,将词体赖以产生的 “文化大市场”归结为四个层面 : “一是宫廷行为,二是文人雅集,三是民间传播,四是寺庙梵唱。”陶先生从四个层面探讨词体起源问题,也充分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词的起源问题虽然复杂,但也是有所遵循的,诚如陶东风所言 : “文体演变既有文学话语自身的规律,也受作家心理、接受者心理以及文化背景的影响。”由此看来,文体学不单单是与作家和授受者有关,社会政治和特定文化与文体的产生与兴衰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为我们探讨隋唐时期的宫廷文化与词的起源及发展问题提供了支撑。而且陶尔夫先生还进一步强调,寺庙梵唱中的道调、道曲的创作动机与宫廷有关,他说 : “这些道曲是不折不扣的宫廷行为,是宫廷统摄扶植的产物,带有明显的颂圣内蕴。”陶先生认为词体起源与道曲有关,而这些道曲又是宫廷文化的产物,陶先生的观点也是我们探究宫廷文化与词的发展关系的铁证。
词与乐(尤其是宫廷音乐)有着不解之缘。曲词的发生是初唐宫廷诗在盛唐的延续和嬗变的结果。词体的发展经历了 “应制—应歌—应社”的过程,其中应制填词促成了词体的宫廷文化书写,比如李白、温庭筠等。宫廷是政治生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也是唐五代文人词创作的重要沃土。
纵观唐五代词的创作及发展过程,作者层是以帝王及宫廷文人为主,他们的词作数量较为可观,质量也可谓上层。这批宫廷词人既是唐五代词创作集体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又因其独特的身份赋予了唐五代词特殊的文化内涵,使唐五代词具有鲜明的宫廷文化属性。宫廷文化为唐五代词人的创作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宫廷器物、宫人服饰、宫廷建筑、宫廷人物以及宫廷宴饮娱乐等成了唐五代词的创作题材,而且唐五代宫廷贵族阶级的审美情趣也得以在词体创作中艺术地呈现。
唐五代时期,宫廷是词体产生、演唱和传播的重要场所。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上编第八章《杂歌与声诗》《歌谣》中有云 : “《一斛珠》等调之始辞,俱是宫体诗。”任先生从词调产生角度强调了词体与宫廷文化的关系;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有云 : “词者,乐府之变也。昔人谓李太白《菩萨蛮》、《忆秦娥》,杨用修又传其《清平乐》二首,以为词祖。盖六朝诸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王世贞先生不仅支持词源于乐府一说,还特别强调六朝诸君臣的“艳语”是“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王世贞所说的六朝“艳语”指的是六朝的宫体诗,其表现内容与词体一致,而且其创作精神也与词颇为一致。细思原因,主要是因为六朝宫体诗与词的共同性都是建立在宫廷文化之上的。
隋代初唐时期虽然在文学文化上有很多先进之处,比如隋炀帝主张文学上要存雅体、归典制,提倡儒家的文学教化传统,但在他统治的后期,一味追求享乐、宫廷音乐变革,催生很多侧艳之歌,与齐、梁、陈时期的宫体艳性诗如出一辙。总之,南朝和隋代文学中的艳语艳声,多与宫廷文化相关,尤其是宫廷宴饮娱乐,创作上具有君臣唱和的特点。
唐人词也与宫廷文化密切相关,具有由帝王出,也由帝王终的特点。唐太宗李世民在历史上是一代文化的帝王,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当大唐盛世辉煌无人能比时,他所想到的是军事上的强大不是真正的强大,他开始着手文化上的建设。他不但聚书立馆,大力提倡文化建设,而且亲自折节 “补课”以弥补当年“躬亲戎事”“不暇读书”之憾。
唐太宗李世民在文学上的主张亦如其《帝京篇序》所说,是 “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走进李世民的诗歌创作,《破阵乐》的慷慨、宫体诗的柔媚、山水诗的清新、咏怀诗的激情 ...... 李世民那瞩望现实、展望未来的丰富心态一览无余,我们感受到的李世民是一个霸王胸襟与儿女情怀的完整结合,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李世民。
但是六朝诗的妩媚对初唐有一定的影响,作为一个血性男儿的李世民,在政治上他有海纳百川、大略雄图的胸襟,这完全是出于一种政治的需要。当他真正地面对自己心灵世界的时候,他又常常掩饰不住自己对宫体诗的倾睐。他对宫体诗的华美很是倾慕,加之君臣宴集的宫廷生活颇多,还有那些宫廷诗人的应制、奉和之作,在富丽堂皇之外,又多柔靡绮艳之篇。虽然他能理性地思考出 “纵情昏主多”的道理,但在感情上他还是无法摆脱六朝那些柔歌艳曲对他的诱惑,他时常自觉不自觉地尝试去写宫体诗。在《唐诗纪事》卷一中曾有记载:太宗“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虽说太宗时期的宫廷之作不可等同于梁、陈、隋,但由于宫廷文化的共同性,也使得闻一多《唐诗杂论》从宫体诗的角度共观之。
由词与宫廷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展望,词作为音乐文学,关于词的起源还要在词与乐的关系上进一步探究。这要追溯中国文学的源头,中国文学原本就是诗乐舞的结合体。纵观诗与乐的发展,其结合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 “由声定辞”;二是“由辞定声”;三是“选辞配乐”。这里的“辞”实际上包括诗、词、曲三种文体样态。对于词体来说,如果没有诗和曲作为参照,词之本质特征也就无从界定。同样,没有词之“别是一家”(李清照《论词》),诗、曲的本体特征也是笼统甚至模糊的。
五代流行的曲子词,其创作风气的直接起源在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有过追述, “对于了解唐五代词发生的音乐与娱乐的背景及其作为一种特定的歌词艺术的性质是十分重要的”。从《花间集序》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的词是一种新兴文体,是一种适应音乐新声的需求所配的歌辞。从所配之乐来看,这种歌辞产生之初首先是在宫廷中流行,然后传播到贵族富豪之家的家乐,甚至于传到了青楼楚馆的伎乐之中。从词体的创作来看,词某种程度上是文人们主动配合乐工与歌女而创作的,既要合于乐,又要便于歌妓演唱。而且其产生环境又决定了词以崇尚绮丽为创作目的,完全是一种新声歌词,而后发展为流行曲词。这恰恰是词与中国传统诗歌体裁的重大区别,随着宫廷音乐的发展变革,词与初盛唐流行的声诗也区别开来了。前文我们提到,唐声诗是乐工取文人诗作的入乐演唱,是先有诗,后配乐,并非文人主动配合乐工歌妓之作,这是诗与词的本质区别。盛唐李白的宫廷应制词和中唐王建的宫词创作体现出了宫廷文化对词体的催生作用。而中晚唐时期(尤其是晚唐)文人与乐工歌妓紧密配合,文人有意为歌妓写词,这明显是诗体创作的一种新形式,也是唐代文人的一种新选择。明初李东阳在探讨诗乐关系问题时曾言 :
诗在 “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乐始于诗,终于律。人声和则乐声和,又取其声之和者以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排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则古之教何必以诗律为哉?
李东阳认为诗乐分离与格律有关,诗乐分离导致诗歌成为有格律而无音韵的 “排偶之文”李东阳所说的“音韵”不是通常意义的平仄黏对之类外在的声律,而是指“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的音声节奏。李东阳的这一论说对于我们了解诗乐分离之后声情并茂的词体产生提供了佐证。
“从词史发展角度看,词作为新兴的文学样式,因受宫廷文化影响和推动,在艺术风貌和审美追求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唐五代词的宫廷文化书写,可以见出皇室贵族和宫廷文人特有的生活环境、情感世界、审美情趣和艺术表现,还可丰富对唐五代社会文化的整体认知,拓展对唐五代文人词的观照视野。”宫廷文化不仅催生了词体,还有力地促进了唐五代词的发展定型与繁荣兴盛。
到了宋代,词体进入了兴盛的黄金期。虽然词体文学风行于市井之中,但宋代的宫廷文化仍旧是宋词创作的渊薮之一。宋代很多帝王喜爱文艺,有的还精通音律,能够亲自创作歌曲。据《宋史 ·乐志》记载,宋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而宋神宗亲自作词赞美所宠幸的宫女 : “武才人出庆寿宫,色最后庭,裕陵得之。会教坊献新声,为作词,号《瑶台第一层》。宋徽宗不仅精通文学艺术,又耽于享乐。他设立了大晟府,形成了以大晟词人为代表的宫廷词人群,迎来了宋代宫廷词创作的高潮。据唐圭璋《全宋词》统计,宋代宫廷词有四百六十余首,书写主体是节序、游宴、寿圣和郊庙祭祀等题材内容。宋代宫廷词不仅拓展了词体的表现领域,也大大提升了词体的社会文化功能。由此可见宫廷文化对词体发展史的重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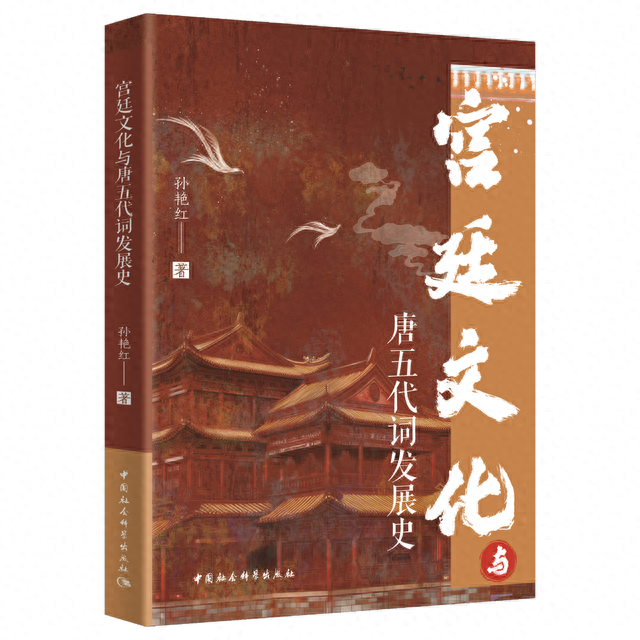
《宫廷文化与唐五代词发展史》
孙艳红 著
ISBN:9787522719009
2023年8月
定价:69.00元
宫廷文化贯穿于唐五代词的发展始终,对词体发生史的建构有重要意义。本书从词的起源问题切入,以唐五代不同发展阶段为横断面,探讨宫廷文化与唐五代词的发展演变关系,具体论述了五个问题:隋代初唐的宫廷文化与词体发生的准备、盛唐的宫廷文化促进词体的形成、中唐的宫廷文化使词体呈现过渡性特征、晚唐西蜀的宫廷文化奠定了词体的基本范式、南唐的宫廷文化促成了五代词的兴盛。唐五代词以宫廷文化为主要题材,具有鲜明的宫廷文化属性。反之,宫廷文化不仅催生了词体,还有力地促进了唐五代词的发展定型与繁荣,进而迎来宋词的大盛。
孙艳红,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吉林省“新文科”建设专家组成员,兼任东北苏轼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辽金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词学会理事等职。主要研究方向:性别诗学与中国诗词史。在《光明日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等报刊上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唐诗经典分类品鉴》等学术专著4部。主持国家社科项目2项,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2项。《稼轩词的女性化风格特征探析》《论韦庄词清丽疏淡的独创性特征》等论著荣获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另外还获吉林省教学成果奖1项,吉林省优秀教材奖1项。
特别声明:本文为北京日报新媒体平台“北京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北京日报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