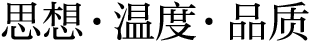在中国的作曲家群体里,有种不成文的“贴标签”做法。一些作曲家被称为“传统派”,一些被冠为“现代派”,少数两者兼蓄,当然也有些学者并不认同这种分类及依据。抛掉体裁的特色、题材的要求和音乐使用场合的限定,以音乐风格划分的传统派和现代派主导着中国音乐的审美标准,也指向了音乐创作的发展走向。无论传统派还是现代派,写的都是现代音乐,两股支流最后都汇入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大江大海。
新作品百花齐放
想要了解现代音乐的走向,理解当下的现代音乐无疑是最好的办法。好在2023年为这一命题提供了绝佳契机。
9月下旬,我在湖北宜昌全程观摩第九届长江钢琴音乐节。一个淅淅沥沥的夜晚,市中心老旧的宜昌剧院正在举行“华夏琴英”钢琴专场音乐会。免费入场的音乐厅内,听众熙熙攘攘,男女主持人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和循规蹈矩的串场词让这场音乐会看上去比听上去更像是一台晚会。
与一般西装革履的男性演奏家有所不同,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葛灏穿着一件颇有夏威夷热带风的花衬衫登台。在一位翻谱员的协助下,他边吼边弹,宣泄之处还时不时从琴凳上蹦起来。不同寻常的演奏和独树一帜的声响让听了好几天《彩云追月》的听众有点抓耳挠腮。即便在场灯熄灭的观众席里仍可看到人们对着钢琴家指指点点,交头接耳,似乎是满脑的问号,又是一脸的好奇。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现场聆听温德青的《情歌与船夫号子》,感受到钢琴家捶胸顿足般的“沉浸式”表演。
今年呈爆炸式态势的现代音乐活动密集上演总计数百部现代作品,由民营企业参与主办的长江钢琴音乐节只是诸多活动之一。从年初到年末,竞相登台的现代音乐盛会不胜枚举。它们有的一年举办一次,有的两年举办一次,有的三到四年举办一次,有的人们已然记不清上一次是在哪年举办。这些林林总总的活动因为各种发展规律和机缘巧合都在2023年登场,呈现出现代音乐一派枝繁叶茂之态。
纵观2023年亮相的现代音乐节或者各类展演,不妨依据主办方或主导方性质把它们分为两类以便讨论。
第一类由政府部门主办、院团主导,包括“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时代交响——全国优秀乐团邀请展演”、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在杭州举办的中国歌剧节、在哈尔滨举办的全国优秀交响乐作品展演、在河北廊坊举办的全国民族器乐展演等。第二类由高校主办或主导,包括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北京现代音乐节、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上海当代音乐节、广西艺术学院主办的中国—东盟音乐周、四川音乐学院主办的成都当代音乐周和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主办的光明室内乐音乐节等。
除此之外,文艺院团如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和甘肃省歌舞剧院,演出场地如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高校如西安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都有成系列的现代音乐演出,这还不包括不计其数的围绕音乐创作方向的闭门研讨和业内论坛。
和古典音乐及海外来团市场一样,现代音乐演出也在2023年迎来传说中的“报复性”增长。
路线和审美之别
虽然这些活动中推出的作品丰富多彩,百花齐放,包罗万象,但通过现场观摩上述绝大多数活动,我总觉得有一条难以察觉的分水岭把中国现代音乐的平原天然隔成两岸,把一些作曲家的阵营自然分为两类,虽然几乎所有作曲家都在或曾在音乐学院任职。简单来说,河道的一边是以政府牵头、院团主导的活动,它们力推的作品大多旋律优美、通俗易懂、引吭高歌,作品背后的作曲家以所谓“旋律派”为纲。河道的另一边是以高校牵头、作曲系主导的活动,它们主推的作品大多随意性大、艰难晦涩、主题多样,创作者以所谓“现代派”为傲。
但就像河道也会改道一样,两个阵营并非不存在某种交互。恰恰相反,一些显著且鲜明的例子证明作曲家融会贯通的能力。作曲家叶小钢和周湘林的代表作成批成群地现身于各类现代音乐盛会的主要舞台上,如周湘林的管弦乐及歌剧作品不仅出现在北京、上海、南宁、成都等地举办的当代音乐节上,也由演出团体主推,被“交响乐之春”、中国歌剧节和全国优秀交响乐作品展演等搬上舞台。
有些作曲家似乎也能徜徉于两种流派之间。当温德青改编自车尔尼的《管弦乐队超级练习曲三首》由菲律宾大学交响乐团年末首演于南宁时,广西文化艺术中心音乐厅内在座的不少同行起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再阅读节目单确认无误后又差一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首温德青听女儿练琴时获得灵感创作的管弦乐小品或可理解为作曲家从现代派向旋律派拐弯,哪怕它只是临时借道的标志,即便作品里朗朗上口的旋律最初来自两百多年前的奥地利。
现场听感留给我的此类印象促使我寻找背后成因。基于甲方决定审美的定律,由政府主办、院团主导的活动需直面大众,有的活动甚至全程在线直播,故而会兼顾社会性和可听性的审美,路线清晰。高校作为学术高地,自然会竖立起探索音乐前沿性的课题,肩负起培养未来作曲家的责任。两者虽然都是现代音乐平台,但侧重点略有不同,就像同在“物理”的屋檐下,会有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之分。
高校是理论研究阵地,既然理论指导实践,高校主办的面向年轻人的音乐比赛或许为现代音乐的未来之路指引方向。2023年高校主办的作品比赛,无论是上海的“百川奖”还是成都的“阳光杯”,其获奖作品均可毫不费力地纳入现代派范畴。这是否是在述说,学术端鼓励的现代音乐必然走上一条让人听来觉得艰深晦涩的不归路呢?
一些学者并不认同对作曲家贴标签式的现代派和传统派的分类,其中就有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教授、作曲家王瑞奇。她认为即便是听众觉得不好听的作品,也有作为作曲家个体探索的意义,“现代音乐也许带着创作者幼稚的思想,也许怀着作曲家天真的偏颇,但它们无一不是作曲家求新求变的体现。从这方面出发,它们都是具有进取意义,富含探索精神的作品,年轻的他们也理应获得理解、包容和尊重。”
天地人和感同身受
有人肯定会说,理想化的做法是传统和现代结合,实验和实用皆取。一批功成名就的作曲家的确可以两全其美。吕其明既刻画了《红旗颂》的万丈豪情,也写出了《庐山恋》的卿卿我我;叶小钢既有《少陵草堂》的历史厚重,也有《玉观音》的诗意抒情。一批包括谭盾在内的作曲家确实从年少气盛的先锋派转向成熟稳健的浪漫派,从而收获到家喻户晓的知名度。如果音乐的长河是由千千万万的个体成长的支流汇聚而成,那现代音乐的出路何尝不会与拔擢才俊的作曲比赛的审美取向背道而驰,最终像作曲家个人成长一样,经历从现代派到传统派的转型呢?
王瑞奇认为,所有的中国作曲家的身上都体现有现代与传统融合的内核,区别只是表现形式。“西方音乐界开拓新音色、新音响以及乐器新功能的探索在20世纪末已基本完成,中国作曲家的诸多独特之处,其中就有使用中国特色的一件或一组民族乐器和世界通行的交响乐团进行抗衡、融合、彰显和转化,这里有很高深的学问,也有很大的潜力。现代音乐的发展方向是雅俗共赏,中西融通,让人感同身受。当代音乐在中国有巨大潜能。”她补充道,“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音乐的未来在中国。”
作曲家的理念固然重要,文艺院团的实践同样关键。身为主要委约方,院团一直是创作背后的推手,现代音乐的未来很大一部分等同于表演团体需要什么样的创作。上海民族乐团团长、古筝演奏家罗小慈提到民族乐器的不同组合会给中国音乐创作带来无限可能性,“一部完整长度的新作,上海民族乐团从和作曲家构思到最后落地演出需耗时数年光景。乐团近年来委约推出的诸如《海上生民乐》《栀子花开了》和《云之上》主题音乐会均在尝试不同的民族乐器组合。民族器乐组合的发展,以及围绕它们的音乐创作,都有很大空间。”
思想性、艺术性、普适性和民族性的兼顾平衡是现代音乐的发展方向。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主任、作曲家陈牧声用一套受老庄之道“天地人和”启发的理论将理想化的中国音乐创作概括之。在他看来,“天”就是符合天道,符合自然规律:“声音的美是有科学性和规律性的,听觉对美的共识印刻在人类遗传基因里。音乐的美、声音的和谐要建立在自然规律之上,此为‘天道’。”由此而来,“地”便具有地域性,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体现,“地是人文环境,民族性体现出地域性文化的影响,包含语言、习俗、生活习惯等。中国式审美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所谓的中国乐派也好,中国风格也好,其本质是受地域文化影响的产物,此为‘地道’。”
在掌握了天道和地道之后,便是人的因素。“这里的‘人’是指对人性的敬畏,对真善美的崇尚。音乐固然是无国界的语言,但前提是要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这就是所谓‘人道’。”在陈牧声看来,天道、地道、人道的和谐统一,是一切伟大艺术作品的重要品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就是这样一部伟大典范和不朽之作。”
当音乐达到天、地、人的圆满境地时,也就是“和”,意味着音乐与宇宙和谐。“这便回到了毕达哥拉斯的理论,他认为数学可以解释世间的一切事物,音乐和谐的法则可以解释宇宙运行的一切规律。”陈牧声说。
或许,这套超脱流派、阵营乃至风格之别,借用古人智慧的理论足以描绘完美状态下的现代音乐走向。但在到达彼岸的漫长实践中,无论是委约方、创作者还是听众群都要保持耐心,给予年轻作曲家充分成长空间,让他们在音乐创作的分流中慢慢体悟融合,日臻“天地人和”。
唐若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