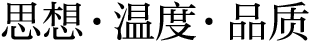导赏,还是不导赏?或者说,音乐会和歌剧演出前的讲解到底有无存在必要?这不仅是我作为音乐会和歌剧听众的疑问,也是作为导赏和讲解者常萦绕于心的问题。
也就是说,导赏者如我,在某种程度上是怀疑着导赏的。但我明显感觉到,近年来对音乐会导赏的需求正日益增加。就在写下这几行文字时,我正在酝酿一星期后中国交响乐团与指挥家林大叶和年轻的钢琴才俊饶灏合作的“乐音致远”交响音乐会的导赏内容。而在5月下旬到6月初这段时间里,我先后为中国交响乐团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两场室内乐音乐会担任导赏和导聆。
作为听众时,导赏有时也会为我带来惊喜期待。几天前,祖宾·梅塔指挥佛罗伦萨五月音乐节管弦乐团的第二场音乐会开始前,国家大剧院演出部项目主管张斯尧在主要涉及观演礼仪的提示中,突然像贝多芬音乐中的转调般将话题转向一个在我看来相当于“迷你导赏”的话题——向听众“剧透”这一晚的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临近结束时,大家将听到一个不一样的华彩乐段,而且会有乐团里的乐器加入演奏。当第一乐章的华彩乐段奏响,定音鼓加入时,由沃尔夫冈·施耐德汉根据贝多芬为他的这首协奏曲钢琴版写下的华彩乐段移植改编的华彩乐段,也成为这一晚音乐会令人瞩目的亮点和难忘时刻。

学生时代听过的音乐讲座,对我理解音乐有很大帮助。当初指挥家李德伦在北京学院路一带的学院礼堂演出时做的那些亲切、易懂的讲解,给我留下美好难忘的印象。后来在伦敦巴比肯中心听到的伦敦交响乐团的多场音乐会,音乐会前的导赏对我的吸引力,甚至不亚于音乐会本身。在我担任中国交响乐团艺术策划部经理的第一年,我迫不及待地希望将我所知的伦敦的音乐会导赏引入我们的音乐季,我的这一建议得到乐团艺术总监陈佐湟的赞许和支持。那个音乐季有导赏的首场音乐会是德国指挥家欧拉夫·科赫指挥的两场音乐会的第一场。让我和乐团惊喜不已的是,在乐团领导左因的邀请下,作曲家吴祖强欣然同意为这场音乐会导赏!
我永远忘不了1998年8月15日那个炎热的仲夏傍晚,我有幸陪吴先生一起走上北京剧院舞台的情景:他抱着两本大开本总谱,那是当晚音乐会演奏的两部交响曲——莫扎特《C大调第四十一交响曲“朱庇特”》和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吴先生的第一句话就让很多听众有耳目一新之感,他指出在两部交响曲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间存在内在联系,不仅赋予这场音乐会的曲目安排内在的逻辑关联,而且激发了大家对即将奏响的两部古典交响杰作不同以往的期待。这么多年过去了,听过无数次音乐会导赏,我自己也做过很多次导赏,最难忘的仍是吴祖强在北京剧院的那次。他对导赏的重视,他作为作曲家在分析前辈大师作品时的那种独特的洞悉力和权威感,使得那次导赏非同一般。
但在当时,以及后来在北京国际音乐节演出中与阿什肯纳齐和佩特连科这样的名家做对话式导赏时,我并未想到,在我们开启了“国家大剧院时代”后,导赏作为与艺术创造有着如此紧密联系的艺术活动,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在现场演出前的导赏之外,还有数量可观的线上演出导赏。交响乐和歌剧,这些被贴上“高雅”“严肃艺术”标签而让太多人望而却步的艺术活动,因为线上演出而变得不那么难以接近,台阶陡然降低。线上演出音乐会或歌剧的观演人数,意味着一场古典音乐会或歌剧的观演人数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在体育馆举行的歌星演唱会。当然,很多人会认为,线上演出的听众需打折扣,有为数可观的人可能心不在焉。但事实上,现场演出中的受众也未必都能心无旁骛、全神贯注。而对于导赏而言,能拥有数万受众,其意义也不可低估。
在我参加的线上导赏活动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2021年12月18日播出的国家大剧院版歌剧电影《玫瑰骑士》。这部歌剧虽然跻身20世纪最受欢迎的歌剧名作之列,但它的剧情、德语唱词,连同剧中三大主角之一“玫瑰骑士”奥克塔维安由次女高音“女扮男”的做法,都需要初次聆听这部歌剧者有一些观演前的知识铺垫。英国作家艾丽丝·默多克在她的长篇小说《黑王子》中就写到作家布拉德利作为在伦敦生活的真正的文化人对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上演的歌剧《玫瑰骑士》的隔膜,他的诧异和困惑的一个来源正是从幕启那一刻就面对年轻的奥克塔维安伯爵竟是由一位女性扮演的。

而在线上演出导赏中,主持人蒋小涵也带着诧异的表情提出这一问题。我们的对话不仅涉及《玫瑰骑士》这部歌剧的这种角色安排,也追溯到歌剧中所谓“裤装角色”这一传统。包括很多观众更加熟悉的“裤装角色”前辈——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中那位凯鲁比诺,还有“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中那位既可以是“裤装角色”也可以由男歌唱家扮演的奥尔洛夫斯基公爵。对于这样的歌剧,演前导赏至少可以解决很多听众心中的疑问,而不必纠结于“为什么明明是女性却非要我相信她是男性”。
虽然无数音乐家从不在音乐会前,更不在演奏进行中加入导赏,但也有些音乐家是赞同和践行导赏的。如维奥尔琴演奏名家和指挥家约尔迪·萨瓦尔,在一次访谈中,虽然强调音乐更应该被聆听而不是藉由文字来传递,但关于是否会用语言向听众解释乐曲的问题,他的回答是“经常会”。尤其是在他的维奥尔琴独奏会上,他会解释他演奏的乐曲,还会介绍他演奏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乐器。他相信“这能让人们离音乐更近”。

既然是这样,那又因何而怀疑导赏的存在价值?当钢琴家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在他的《钢琴家和曲目》一文中写到他的伟大前辈同行李斯特作为独奏会这一演出形式的初创者在演奏中与听众交谈(导赏)的做法时,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所幸这一习惯今日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布伦德尔并不认为演奏者的导赏讲解有任何必要。其观点背后,应该是这位思想敏锐的当代音乐家意识到语言与音乐不同,正如尼采指出的:“当我们全身心地投入音乐时,我们的大脑里没有文字,那是一种极大的放松。一旦当我们回到文词,并试图得出一些结论,我们对音乐的感觉立时立刻就变得肤浅了,我们将之概念化。”尼采的这一洞见并非他的独特发现,梅纳德·所罗门在《贝多芬传》中写道:“音乐的内容无法迻译成文字,这在哲学家中间是老生常谈。”他引用另一位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表述:“因为音乐表达的始终是全然直接中的直接……因此没有可能用语言说明音乐。”而导赏、导聆、讲解,正如节目单上的乐曲解说,难道不是在“用语言说明音乐”?
从我得到的听众反馈来看,“用语言说明音乐”的导赏还是颇受很多听众欢迎的。在2022年金秋时节演出的“管中乾坤——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木管五重奏”音乐会上,我有幸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五位管乐演奏家同台,听众脸上的表情给我的感觉是:在星期天上午到国家大剧院听一场周末音乐会,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瑶族舞曲》、《魔笛》序曲等一系列优美悦耳的中外乐曲演奏以及我穿插其间的讲解结束后,我收到了负责周末音乐会组织的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教育部部长陈戈转来的一位听众的评价,这位听众特地提到了“导聆”:“所有的讲述都是从心底如清泉般涌出,听众很轻松地跟随他的指引进入演奏家引领的音乐世界……”这是我迄今读到的对于我作为导赏者的最美褒奖,也让那个“导赏,还是不导赏”的哈姆雷特式疑问有了向前者倾斜的答案。
王纪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