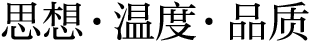编者按:今年是李大钊同志诞辰135周年,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一生的奋斗历程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紧密相连,他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播撒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知所从来,方明所往,“北大红楼”特推出【回忆李大钊】专栏,与您共同缅怀致敬“播火者”李大钊。
1915年初,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后,结识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经李大钊介绍,许德珩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和邓中夏等人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以扩大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李大钊身着洗得褪了色的布料长袍,诚朴谦和、热情地回答大家提问的形象,永远铭刻在许德珩的心里。那时,许德珩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很多文章,直到晚年,他仍能背诵《青春》一文中的很多警句,如“冲决历史之桎梏,荡涤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许德珩说,每次背诵,都为大钊同志气势磅礴、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所鼓舞。今天,我们通过原载于《光明日报》(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许德珩所撰写的文章《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一同回顾李大钊为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
许德珩
一九一九年元旦,大钊同志在《国民》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尖锐地揭穿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侵略的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这是我国第一次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钊同志还鲜明地提出必须要“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中国和亚洲,然后与世界各民族结成“大联合”,从而“益进人类的幸福”。
与此同时,大钊同志和陈独秀又举办了一个《每周评论》。鲁迅、高一涵、张申府等人都在这个周刊上投稿,对五四运动也起了积极作用。
“五四”前夕,北大虽然成立了若干社团,但是由于各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倾向,因而彼此之间隔阂甚深,甚至不相往来。最令人折服的是,大钊同志把北大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社团,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一共同点团结起来,组织在一起。如“五四”前,他动员新湖杂志社的罗家伦、康白情加入北大学生会,并说服我们允许他们参加。由于大钊同志的调解和促进,从而北大学生团结起来了,成为五四运动的一股主要力量。
团结在大钊同志周围的、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一部分爱国青年,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这时已经常在一起活动。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越来越露骨,咄咄逼人,民族危机日益紧迫和严重;由于军阀政府腐败不堪,软弱无能,我们深感宣传、教育、出版等等行动不能满足斗争形势的需要了。我们在大钊同志的办公室里,越来越经常地讨论着一个问题——“直接行动”。“直接行动”,是大钊同志向我们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情况时多次提到的,即不经当局同意批准,发动群众,直接采取正规范围以外的行动,以达到革命的目的。斗争的实践也使我们深深感到同帝国主义和军阀搞合法斗争是行不通的,一九一八年五月请愿运动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和鼓舞着爱国青年中的核心分子,从而迅速传播到广大学生中去,即将到来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大风暴就是这样在酝酿着。而大钊同志在“五四”前夕的文章中,第一次把“直接行动”公开地提了出来,这实际上是五四运动到来前的一个信号。
“五四”前,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钊同志,通过学校、报刊、社团以及到各地的讲演等活动,联系了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在为五四运动进行思想准备的同时,也在这个运动的组织准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运动中,大钊同志发表文章,正确地指出我们的仇敌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卖国的也不仅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几个人。所以,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是达不到目的的。我们必须“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把这强盗世界推翻”。这种看法,对于五四运动坚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方向是大有益处的。
五四运动的斗争,致使北洋军阀政府恼羞成怒,进行反扑。在他们的逼迫下,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辞职出走。爱国青年的活动内容,又加上了挽留蔡校长复职,反对胡仁源来校(反动政府派胡仁源代北大校长)这一强烈要求。大钊同志等北大教职员代表,于五月十日向北洋政府交涉,坚决挽留蔡元培先生,更广泛地发动教职员,和广大学生采取同一步骤,把学生和教职员也团结在一起了。
大钊同志在“五四”前就号召我们:“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五四运动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大钊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北京学联派我和黄日葵同志南下,同各界联络。由此,参加五四运动的就不只是知识分子了,而是成为一个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妇女界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蓬勃进展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迫使反动军阀政府在六月七日释放了几千名因街头讲演而被捕的学生,十日批准曹、章、陆“辞职”。
在此期间,北京城里出现了《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这是大钊同志和陈独秀等散发的。宣言中要求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废除反动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的密约;指出卖国贼除了曹、章、陆之外,还有经手向日本借款和购买军火的徐树铮,镇压群众运动的段芝贵、王怀庆;并提出取消步军统领和警备司令部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市民须有绝对的集会、言论自由权。
六月十一日,大钊同志带领两人去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同时,陈独秀、邓初(内务部佥事)、高一涵三人去新世界散发传单。就在这天,陈独秀被捕。大钊同志立即设法营救陈独秀,于当年九月出狱。及至阴历年底,陈独秀仍为警察厅所监视,待不下去了,大钊同志挺身而出,化装成北方商人模样,驾上一辆骡车,让陈独秀坐在车里,顺利地护送陈独秀出京。大钊同志这种有勇有谋的革命精神,真令人钦佩。
大钊同志热心帮助和接济同学的事迹,常为大家所称道。大钊同志经常把自己的月薪拿来帮助清苦同学。记得刘仁静同学因经济上拮据,一时交不了学费,大钊同志就出具证明,请学校准予缓交。这个证明现在仍然保存在北京大学的档案之中。
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我赴法勤工俭学之前,大钊同志对五四运动给予的高度评价。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国民杂志社成立一周年,举行纪念会,并欢送我和陈宝锷赴法勤工俭学(陈宝锷后来并未去法,而是到了英国)。是日到会者除社员七十余人外,尚有来宾李大钊、陈独秀、蓝公武及徐宝璜。大钊同志在会上发表演说,大意谓:“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诸君本此进行,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勉旃!”
但是,这次欢送会上同大钊同志聚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底,大钊同志死难的噩耗传来,宛如青天霹雳,使我悲痛异常。当年欢送会一别,不料竟成永诀。
一九二七年五月,我正在武汉,大钊同志牺牲的消息传来,在武汉的同志举行了沉痛的追悼会。我以北大校友的资格,在会上讲了话。诚如何香凝同志回忆的那样:当我们“在汉口开会,听张太雷先生报告李大钊先生殉难的经过,我们都不能遏制地流下眼泪来”。
一九三三年,党通过北大师生和他的生前友好,发起为他举行公葬。为这一公葬捐款的知名人士,有鲁迅、李四光等一百多人。我当时不在北平,回来后,特地到香山之下万安公墓去凭吊大钊同志,以表示我对大钊同志的深切怀念和爱戴。
陈毅同志在一篇纪念大钊同志的文章里,对于大钊同志的一生概括了十六个字:“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革命先驱,大节不辱”,我觉得十分中肯恰当。
大钊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来源:摘自人民出版社出版《回忆李大钊》(1980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