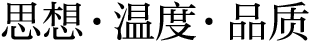歌德曾用“戴着镣铐舞蹈”来形容诗人需在考虑格律限制下进行创作的不甚自由的状态。对于指挥家来说亦是如此,个人的巧思必须要在对谱面信息谨慎的遵循与对作曲家精神意图精准表达的夹缝中寻求抒发,在本真中探寻个性、在严格中发现自由。
12月6日,荷兰指挥家梵志登首度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携手华裔钢琴演奏家陶康瑞、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小号首席王与兵,以瓦格纳、肖斯塔科维奇与贝多芬三位浪漫主义音乐巨匠笔下宏大的时代之声,奏响国家大剧院建院17周年音乐会。这三位作曲家的音乐皆以宏大的叙事主题与深邃的人文精神著称,但本场音乐会却选择了其创作中并不常规的“喜剧”经典——瓦格纳惟一的喜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序曲、肖斯塔科维奇的青春之作《c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以及有着“舞蹈性”交响曲之称的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梵志登在这三部以轻松欢快、诙谐风格著称的选曲中展现出了德奥音乐高度严谨的态度与深邃的浪漫主义精神。
《纽伦堡的名歌手》序曲是梵志登在今年巡演中经常上演的开场曲目,在他干练刚健、毫无冗余的指挥下,这首序曲中充满活力的愉悦气质恰到好处地流露而出,主题间的过渡流畅而不呆板。梵志登对于管弦乐队音色、音质及响度配比的把控有着近乎于外科大夫般的精准和严谨,这使得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能够将木管与铜管的独特声音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使在以丰富的弦乐为主导的段落中,听众也可以清晰地捕捉到管乐的旋律线条。这一点展现出梵志登对瓦格纳音乐中交响性的敏锐感知与深刻理解,这首欢腾的序曲并没有走向喧闹的失控,而是在各乐器声部“暧昧”的融合中共鸣。

肖斯塔科维奇的《C大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是这场音乐会的一大亮点。小提琴演奏家出身的梵志登对弦乐声音的控制令人惊艳,在协奏曲中他为弦乐组设立了一个绝对的音量阈限,高音流畅而不会过于明亮,中低音深沉却不厚重;既可以在无独奏乐器的段落中饱满地呈现出音乐情绪的丰富性,又不会由于过强而喧宾夺主。同时,梵志登十分强调节奏的严谨性和紧凑,然而在这样相对约束的条件下,弦乐队仍可以很好地表现出在抒情、沉重、诙谐和紧张几种情绪间的转换与鲜明对比。在全曲大多数时间内,弦乐以一种几乎“沉闷”“模糊”的弱音响度将中心让渡于钢琴和小号,即使是在强奏处仍旧如此,恰当地突出了两件独奏乐器的音色个性。陶康瑞的钢琴演奏干净利落,尤其是对于延音踏板的掌握,他能够精确地依循乐句的动态收放自如,在严密的节奏中表现出爵士乐般的松弛和放纵。在如此鲜明的音响层次中,小号的表现力获得了极大的拓展。特别是在第二乐章,弦乐的“让位”使得小号能够在相对不甚明亮的音色下恰当地实现音乐表达所需要的抒情性与歌唱性。

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中,梵志登依然延续了其严谨的态度,他对节奏严格进行的苛求不仅让人联想到阿什肯纳齐的指挥风格。其优势在于能够赋予音乐强大的行进动力,而弊端则是牺牲了一定的表现力。第一乐章的首个和弦并没有预期当中的那样清晰,梵志登的处理与他在指挥界的领路人伯恩斯坦相似,他以一种“嗡鸣”式的音响开始,从而更好地衔接双簧管的长音线条,这种做法虽然使旋律的进行更加具有延续性,但似乎还是小克莱伯那种果断利落更令人满意。当然,凭借他快速的节奏和音乐驱动力的巨大冲动,梵志登在引子部分的表现相当不错,活泼主题的运动感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引子之后进入呈示部主部主题时,长笛与弦乐的对话却稍显平庸,长笛的音色特点没有获得突出,而弦乐的回应则更显“朴素”,从而缺乏了这种问答式动机应有的俏皮与灵气。梵志登严格的节奏处理显然更适用于最为著名的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中,固定低音的节奏带来了强大的内在动力,不断推进着音乐由哀伤走向歌唱、辉煌直至沉默。在节奏规则的制约下,梵志登似乎来到了自己的舒适区,他会在某一乐句伊始将节奏伸展、拖延,而后通过快速的进行补全该节奏进行的单位时间。这样自由节奏化(Rubato)的处理极大丰富了乐曲的情绪张力,也为个性化表现创造出了空间。在随后的第三、第四乐章中,梵志登更加放大了这一特点,其在松弛和紧张中的游离转变更加凸显了音乐舞蹈般的活力与谐谑气质。由此,梵志登实现了在交响曲精密的规则分寸中个人浪漫主义的表达,宛若“戴着镣铐舞蹈”。

在以往的评论中,经常可见到对于梵志登节奏控制的批评与驳斥,但当晚的表演已经向听众证实,经过在纽约爱乐和港乐多年的耕耘,如今年逾花甲的梵志登已能自如地在分寸方圆中展现其独特的个性,在他“宫廷乐长”般的严谨威严背后,亦是一个浪漫的灵魂。对于今年这场国家大剧院首秀来说,以瓦格纳为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写下的评价作为总结再适合不过——“所有的骚动,所有的渴望,所有心灵的风暴,在这里都变成了快乐的狂欢,它以狂欢的力量带着我们穿越大自然的广阔空间,穿越生命的溪流和海洋,当我们在宇宙中响起这支舞蹈般大胆的乐章时,我们在快乐中欢呼雀跃”。

张浩哲/文
王小京/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