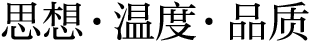1989年12月5日上午,时任北京日报的S副总编告诉我:“严新约你去当面谈谈。”我正想会会这位“大师”呢,便毫不犹豫地说:“可以,什么时候?”S副总编说:“今天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王××陪你一起去。”
严新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气功大师。他为什么要约我一个小编辑去谈谈?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这年10月14日,我采写的《气功师“山泉公”骗人害命 十九岁少女活活饿死》刊发在北京日报上。

报道说的是本市北三环路边某机关家属院,有个19岁的少女,跟她母亲一起,听信一个气功师的鬼话练“避食功”,最后各器官衰竭而死。我采访后得知,跟这个“山泉公”练“避食功”而死的至少还有两个人。气功师如此害人、一些群众如此愚昧,令我震惊。我决心揭露伪气功实质、唤醒群众不要再被骗。我约请几位记者采写了一系列稿件,经我编发,陆续在北京日报周末版上刊出。这些稿件是:
10月21日,记者钟卫宁:《专家认为:“避食功”缺乏科学根据》;记者孙瑛:《清华大学科研处负责人说,赞成以科学态度研究气功,反对神秘化;一些“研究成果”未经鉴定与学校无关》(此前《健康报》已有一篇同样内容的报道)。
我在前一篇文章后面加了编者按:“据了解,现在仍有一些人相信‘山泉公’,在练他的‘避食功’。我们劝这些人以自己身体为重,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冒险了!有病还是应该去求医为好。”后一篇则是为澄清一个事实:严新与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搞的“气功外气对2000公里超距离物质分子作用的实验研究”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所谓的“实验研究”使很多人对气功师能发放“外气”深信不疑。而在这篇报道里,清华大学科研处的负责人说:清华大学确有一些教工在研究气功,但只是个人的活动;严新与科研协作组做的实验,没有校方负责科研的人员在场;所发表的东西也未经申报、鉴定,谈不上是科研成果。
10月28日,记者钟卫宁:《市卫生局:中医局从未批准过任何私人气功师行医》。这篇报道等于宣布:所有在京行医的私人气功师,行医都是不合法的。
11月4日,记者杨立君:《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专家张洪林认为:“外气”治病是一种暗示疗法》。为什么气功师发放“外气”能在患者身上产生作用?张洪林揭示出了实质:是暗示在起作用。张洪林让去拍照片的摄影师刘凯旋穿上白大褂,对来看病的患者说,这是一位功力很强的气功师,现在请他为你发功治病。然后摄影师刘凯旋便按照张洪林教给的方式给患者“发功”,患者果然收到了他的“功”,有了很强的感觉!事实证明,不是“外气”在起作用,是心理暗示在起作用。这篇报道见报之后,不断有人去拜访张洪林,有去求教的,也有去挑战的。求教的,大都被张洪林的观点所折服(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司马南);挑战的,无不铩羽而逃。这是后话。

我本人也是在这篇报道之后,才知道了发功治病的实质。因为我学过医,知道心理暗示也是某些疾病的有效治疗方法,所以张洪林的理论对我来说就像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11月11日,《带功讲课的秘密何在?有人搞了一个有意思的试验》——这篇报道是我采写的,署名甄石,采访对象是湖南衡阳杂技团团长孟继孔。几个月前,他带着他的团在天坛公园内演出,看了我们的一些报道后主动来找我。他说他听过严新大师的“带功讲课”(门票10元一张——当时可以买12斤猪肉!首都体育馆一次可容纳1. 73万人。在那段时间,“带功讲课”几乎天天都有。“讲课”的录音盒带也卖钱,50元一盒),看到有现场听课的人又哭又喊、如醉如痴的样子觉得好笑。于是他回到长沙也照着严新的样子搞了一场“带功讲课”,效果比严新的还好,40%的听者有了剧烈反应:哭的,笑的,呕吐的,满地打滚的。也有人远距离接收到了他的“外气”,事后向他汇报说:关节炎被治愈,腿疼的病好了!不过孟继孔没有自称为大师,他向所有人宣布:我不是气功大师,我也不会发放“外气”,你们的反应,是接受了我的暗示的结果。
这些报道,显然触动了严新大师。他不知有何“背景”,担心是哪一位领导发了什么指示。于是便托人打听。我后来得知,他请了两位本报的记者吃了一顿饭,了解到这一系列的报道不过是一个姓宗的小编辑组织的!于是,严新通过中央台女编辑王××,联系到了S副总编。S副总编要我去严新那里,跟他谈谈。
我想找个记者陪我一同去。不是我胆小害怕,而是想找一个见证者。理论部一个记者听说要去见严新,吓得连连摆手,说:“我不敢去,你还是一个人去吧。”
我不是一个人去的,陪我一同前去的,是报社车队的司机赵金生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