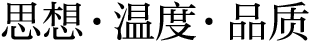明代,北京内城的格局已经基本定型,东四一带是热闹的商业区,而朝阳门又是当时重要的城门,从朝阳门去往通州,那会儿没有汽车、地铁,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驴和骡,一来二去,在朝阳门附近就形成了一个专门交易驴骡的市场,久而久之,人们就顺口叫它“驴市胡同”。清康熙年间的《帝京舆图》(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清代早期京城实测地图)上,清清楚楚地标注着“驴市胡同”四个字,而清代官修《顺天府志·卷七·城池》中还特意补充了一句:“驴市胡同亦称‘骡市’。”
除了驴骡交易,胡同里还有不少配套的行当,挨着牲口市场的地方,有钉铁掌的铺子,墙根底下,还有摆摊给牲口瞧病的兽医,还有来回串游的皮革贩子,背着一捆捆皮革,嘴里吆喝着“收皮革喽——收旧皮靴、旧皮袄喽——”。还有一些江湖艺人,趁着牲口市场人多,就在胡同口搭个小台子,表演杂耍、说书,有耍猴的,有吞剑的,还有说书先生讲《三国演义》《水浒传》。每到逢年过节,驴市胡同就更热闹了,商贩们会在胡同两边摆上摊子,卖糖葫芦、卖糖画,孩子们穿着新衣裳,在胡同里跑来跑去,手里拿着糖葫芦,嘴里嚼着糖画,笑声、欢呼声、吆喝声混在一起,成了老北京最鲜活的烟火气。
这种热闹的景象,一直持续到清末宣统年间。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力车慢慢兴起,取代了驴骡,成为京城主要的交通工具,驴骡的需求量越来越少,驴市也渐渐冷清下来,到最后,干脆就废除了。驴市没了,“驴市胡同”这个名字,就显得有些俗气了,毕竟那会儿,这条胡同里已经住了不少官员和文人,大家觉得,“驴市”这两个字,配不上胡同里的文雅气息。于是,有人就提议,借着“驴市”的谐音,把胡同改名叫“礼士胡同”,“礼士”二字,取自“礼贤下士”这个成语,寓意着尊重贤才、礼遇士人,既文雅,又符合当时胡同里的氛围,这个提议一出来,就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据《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志》记载,“驴市胡同”于清宣统年间正式改名为“礼士胡同”,一直沿用至今。
胡同的名字,就是胡同的脸面,改个名字,就意味着胡同的气质变了,从一个充满市井气的牲口市场,变成了一个崇文重礼的文人雅士聚集地。
早在驴市还热闹的时候,这条胡同里就已经有不少贤达之士居住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清代的大学士刘统勋和他的儿子刘墉,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刘罗锅”。据清代礼亲王昭梿所著的《啸亭杂录·卷二·刘文正公》记载:“刘文正公赐第在驴市胡同西头,南北皆有院,甚湫隘,不似大臣之居。”明确说明刘统勋的赐第就在驴市胡同西口,南北有两个小院,规模不算特别大,但十分雅致,透着一股清廉之气。《清史稿·卷三百二·列传八十九·刘统勋》里明确记载,刘统勋是山东诸城县人,雍正二年(1724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从此踏入仕途。乾隆元年(1736年),他升任从二品内阁学士,之后历任侍郎、尚书、军机大臣,直至正一品大学士。
刘统勋去世后,他的儿子刘墉继承了他的衣钵,也住进了驴市胡同的这所宅院里。刘墉这个人,大家都很熟悉,他身材矮小,后背有点驼,所以民间都叫他“刘罗锅”。他才华横溢,书法造诣极高,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清代四大书法家”。《清史稿·卷三百二·列传八十九·刘墉》记载,刘墉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之后历任知府、巡抚、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大学士,和他的父亲一样,深受乾隆皇帝的信任。在担任湖南巡抚期间,兴修水利、整顿吏治,政绩卓著。他在担任大学士的时候,办事认真、公正无私,不管是朝中的大事,还是百姓的小事,他都一丝不苟,尽力去做好。而且,他一生清廉,和他的父亲一样,家里没有多少钱财,房屋也还是那所乾隆皇帝赏赐的宅院,没有特意扩建,也没有装修得富丽堂皇。
刘墉去世后,他的孙子刘环之,也住进了这所宅院里。《清史稿·卷三百二·列传八十九·刘环之》记载,刘环之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之后历任户部尚书、顺天府府尹,虽然才华不如刘统勋和刘墉,但也算是一位称职的官员,嘉庆年间,因“政务偶有疏失”被降职,之后就渐渐淡出了官场。据说,刘环之去世后,刘家就渐渐衰落了,这所宅院也几经易手,后来,就被别人买走了。
除了刘统勋、刘墉父子,礼士胡同里还住过不少贤达之士,清末的军机大臣世续,就是其中之一。《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三·列传二百六十·世续》记载,世续为满洲正黄旗人,历任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是慈禧太后身边的股肱之臣,为人精明、圆滑,很会揣摩慈禧太后的心思,深受慈禧太后的信任。他一生经历了清末的很多重大事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在辛亥革命后,率先表态赞成宣统逊位,并受命磋商优待条件。据《清宣统朝实录》《辛亥革命史料汇编》记载,辛亥革命爆发后,全国上下都要求清帝退位,结束封建帝制,朝中的大臣们分为两派,一派赞成清帝退位,一派反对清帝退位,双方争论不休,僵持不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世续站了出来,率先表态,赞成宣统逊位,他认为,时代已经变了,封建帝制已经走到了尽头,继续坚持下去,只会让国家陷入更大的混乱,让百姓遭受更多的苦难,不如顺应时代潮流,接受共和,这样,既能保住皇室的体面,也能让国家早日安定下来。世续的这个表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他的带动下,不少朝中大臣也纷纷表态,赞成清帝退位,最终,宣统皇帝颁布了退位诏书,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世续也因为这件事,被后人称为“识时务、知变通的官员”。
礼士胡同里,还住过一位中国现代眼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他就是毕华德。据《中国医学通史·现代卷》记载,毕华德(1891—1966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就留在协和医学院任教,后来,又远赴著名的维也纳大学眼科进修,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可是个真正的“洋博士”,精通英语,学识渊博,但他却打破了多年的传统,率先使用汉语授课。他觉得,医学是为百姓服务的,不能因为语言的障碍,就让很多有才华的医生无法学习先进的眼科知识,于是,他毅然决定,改用汉语授课,还把自己的授课讲义,翻译成汉语,供学生们学习。他的这个举动,受到了很多医生的欢迎和尊敬,也为中国现代眼科学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还有一位抗日名将,也曾在礼士胡同居住过,他就是郑洞国将军。《郑洞国回忆录》《中国抗日战争史》记载,郑洞国将军(1903—1991年)毕业于黄埔一期,是一位英勇善战、爱国爱民的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领部队,先后参加长城抗战、台儿庄战役、昆仑关战役等,奋勇杀敌,抗击日本侵略者,立下了赫赫战功。抗日战争胜利后,郑洞国将军担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驻守长春,但他深知,内战只会让百姓遭受更多的苦难,所以,他一直反对内战,希望能够实现和平建国。后来,在解放战争中,郑洞国将军率领部队,脱离了国民党阵营,宣布起义,投向了人民的怀抱。毛泽东主席得知后,十分高兴,特地电示东北局,对郑洞国将军“应给以礼遇”(该电文收录于《毛泽东文集·第四卷》)。郑洞国将军来到北京后,目睹了新中国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深受感动,主动表示,愿意参加祖国的建设,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的这个请求,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嘉勉,也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毛泽东主席还特意在家里设宴,招待了郑洞国将军。
除了这些官员和名人,礼士胡同里还住过不少文人墨客,诗人邵燕祥,就是其中之一。邵燕祥在《邵燕祥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中明确写道:“我出生在东四礼士胡同。”他自幼生活在这条胡同里,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对这条胡同,对这座京城,有着深厚的感情。邵燕祥曾经在文章中,回忆过自己在礼士胡同的生活,他说,胡同中段路南,曾有一条窄巷,连通着演乐胡同,名叫南下洼,正对其北口的礼士胡同北侧,有一条死胡同,名叫双堆子大院。他还解释说,“堆子”是过去打更人过夜的房子,还有一种说法,是京城清八旗兵的驻屯之所,“双堆子”,就是有两个这样的堆子。不过,让他感到奇怪的是,他小时候在胡同里生活,经常听到老人们说起胡同里的两座大庙,却从来没有在文章中提起过,这两座大庙,就是昭宁寺和常宁寺。
据清末缪荃孙编撰的《燕都丛考·卷三》记载:“报恩寺在驴市胡同街北,不知何时创建,明朝天顺元年更寺名曰昭宁寺(又名常宁寺),大学士李贤撰碑,碑已无存。”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昭宁寺的前身,是报恩寺,创建年代不详,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被改名为昭宁寺,还有一个名字叫常宁寺,当时的大学士李贤,还为这座寺庙撰写了碑文,只是可惜,这块碑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李贤为明代名臣,《明史·卷一百七十六·列传六十四·李贤》有传,其撰碑之事可佐证寺庙的历史地位。)
关于这两座寺庙的始建年代,还有一些争议,两次民国调查的记录不一,一说不详,一说均始建于明嘉靖二年(1523年),但这与史料的记载,出入很大。清代吴长元编撰的《宸垣识略·卷七·内城四》中记载,报恩寺内有大钟,大钟上铸着“昭宁寺”三个字,小钟上铸着“报恩寺”三个字,这说明,这座寺庙最初的名字是报恩寺,后来才改名为昭宁寺,而改名的时间,是天顺元年(1457年),比嘉靖二年早了六十六年。之所以会有嘉靖二年的推断,可能是因为当时,这座寺庙进行了一次大修,留下了一些相关的器物,人们误以为,这座寺庙是在嘉靖二年始建的。
据考证,昭宁寺在《乾隆京城全图》(清乾隆十五年绘制,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标注在小十字路口西北角,而对照民国调查的记录,这个位置,后来变成了常宁寺,常宁寺的山门,临着礼士胡同,昭宁寺则在常宁寺的东北侧。有人推断,最初,报恩寺改名为昭宁寺后,规模渐渐扩大,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到万历年前,就从昭宁寺中分出了一部分,形成了独立的常宁寺,也就是说,常宁寺最初,是昭宁寺的西廊,后来才慢慢独立出来,成为一座单独的寺庙。两年前,有人曾经对这两座寺庙的位置,进行过几次查访,终于明晰了它们的具体位置:小十字路口西北侧的方块区域,就是常宁寺,在如今的117号院处,开有一扇小门,东南角,还开有一个大门,当年,香客们大多从这个大门进入寺庙。常宁寺内,有地藏殿,还有一排十余间的西寮房,开有后门,东侧还有一个侧门,通往昭宁寺。昭宁寺的山门,则开在北口,如今85号院的水平位置,正对着南下洼,两座寺庙的南北分界线,就在这里,昭宁寺的北侧,一直延伸到前炒面胡同,后殿的位置,就是如今的楼房所在地。
礼士胡同里,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宅院,就是位于胡同中部的129号大宅门,这座宅院,规模宏大,建筑精美,是礼士胡同里,最为醒目的宅院之一,很多人都以为,这座宅院,是清代官员刘墉的故居,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据北京市东城区文物局1991年出版的《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卷》明确记述,礼士胡同129号,是清末武昌知府宾俊的宅院,宾俊去世后,他的儿子锡琅,是个败家子,不务正业,沉迷于吃喝玩乐,很快,就把家里的钱财,挥霍一空,无奈之下,只好把这座宅院,卖给了别人。(宾俊为清末官员,《武昌府志·晚清官员名录》有其任职记载)
这座宅院,第一次转手后,卖给了一位大律师江颖,但江颖在这里住的时间,并不长,没过多久,就又把这座宅院,转手卖给了天津盐商李善人之子李颂臣。李颂臣是个很有品味的人,他买下这座宅院后,并不满意宅院的原有格局,于是,就请了朱启钤的学生,重新对这座宅院,进行了设计和改造。他们按照南方园林的风格,对这座宅院,进行了改造,在宅院里,修建了假山、池塘、亭榭,种植了花草树木,让这座北方的四合院,融入了南方园林的雅致与幽静,既有巧夺天工的人工建筑,又有怡然幽静的花木之胜,成为当时礼士胡同里,最精美的宅院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座宅院,曾经作为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后来,又成为中国青年报社的社址,再后来,又成为电影局的办公地。1984年,这座宅院,被确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年,电视连续剧《大宅门》摄制组,就是看上了这里的“大宅门”气派,把这里,作为拍摄外景地,这座宅院,也因为这部电视剧,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除了129号宅院,礼士胡同里,还有不少有名的宅院,比如,胡同东口路北123号院,是清代大学士敬信的旧居,《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三·列传二百三十·敬信》记载,敬信为满洲正白旗人,历任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为官清廉。民国时期,这里曾经做过蒙藏院(见《民国政府机构沿革史》),如今,这里是礼士胡同小学。